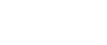朝核危机,安倍修宪,台湾民进党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表态,南海争议等这些国人最关注的时政要闻,究其根源,都和一位美国将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是他首次提出美国的战略重心或优先级应该转移至亚洲,是他主导了战后对日本的改造,其主持通过的和平宪法为日本战后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他坚持出兵朝鲜半岛,将朝鲜几乎要到手的统一全国的胜利果实毁于一旦,令南北双方至今处于枕戈待旦的状态,其中一方近年来因为生存焦虑更是频频核试造成地区局势不稳;是他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敌意,并号召强力支持溃逃到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并利用朝鲜战局极力升高两岸军事对抗状态,导致至今海峡两岸在“三通”经年后仍未签署军事层面的和平和互信协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几乎凭一己之力奠定了东亚二战后的格局,至今仍未被打破和颠覆。很难再想象还有哪一位美国将军比他的政治遗产对中国的影响更大,更长久,更深远。他就是麦克阿瑟。
在人们的认知中,麦克阿瑟长期是作为一个囿于意识形态偏执的战争贩子的面目出现的,从这一点出发,他的很多作为就比较“自洽”:他“不负责任”地赦免了天皇的战争责任,起复了很多战前日本政府的官僚,打压日本农工运动,对红色中国充满敌意,把朝鲜半岛的局势看成共产主义阵营的新攻势,不顾杜鲁门总统的劝阻一意孤行将战火扩大到中朝边境,在中国志愿军已经卷入朝鲜战事的情况下还不愿收手,一意孤行扩大战事,极力主张将在台湾的国民党部队投入朝鲜战争等等。最后,他终于落得了个被杜鲁门撤职并“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这一我们耳熟能详的逻辑之外,哪怕是本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精神,看看麦克阿瑟自己是如何解释其所作所为或换言之如何为自己开脱的,依然是有价值的,因为虽然经过近几十年的密切交往,中美间战略误判的可能依然存在,而类似麦克阿瑟这样的战略研判和战略思维逻辑在美国依然有着其拥趸。《麦克阿瑟回忆录》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照切口。
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的最大分歧在于欧亚两个战场孰轻孰重的问题。当时美国政府主流意见认为和苏联抗衡的主战场是欧洲,如果在亚洲投入太多的人力物力,则正中苏联下怀,所以才有了后来著名的所谓“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那段话。而麦克阿瑟显然不这么看。这说到底也是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关于欧洲和亚洲优先级问题分歧的延续,当时马歇尔等人力主并被付诸实施的“先欧后亚”始终令麦克阿瑟耿耿于怀。
在那篇于国会发表的著名演说中,麦克阿瑟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战略考量,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众声喧哗之下情绪激昂的民众更多把注意力投向了“老兵不死”这一悲情主题。在这篇演说中,麦克阿瑟高度评价了亚洲重要的战略地位:拥有地球上一半人口和 60% 自然资源的亚洲民族正在迅速凝聚成一股精神和物质意义上的新势力。世界经济前沿阵地正在转移,世界事务的中心也正在转回其初始区域,因此美国必须调整自身政策来顺应这一基本发展趋势。麦克阿瑟的这番话像极了美国政府近年来为其“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展开的说辞,仿佛是过早的过于正确的预言。
在此认知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在二战期间为“解放亚洲”所做出的巨大努力,麦克阿瑟要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画上一条新边界。如果说此前美国西侧的战略前沿是美洲的西海岸,以及从夏威夷、中途岛、关岛延伸到菲律宾的“暴露在外”的脆弱突出部,随着美国在太平洋的胜利,其战略前沿移到了整个太平洋,通过控制从阿留申群岛延伸至马里亚纳群岛的弧形岛链,并从这个岛链出发用海空力量控制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新加坡的所有亚洲海港,美国的西部边界从美洲的西海岸转移到了亚洲的东海岸,从而使整个太平洋变成了一条保卫美国利益的“巨大的护城河”。毋庸讳言,迄今这条岛链依然是中美双方海空力量博弈的物理和心理对抗线。
而且,在麦克阿瑟看来,“共产主义威胁”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在任何一个区域的成功进展都会令其他区域面临毁灭的危险,因此在亚洲对其姑息或屈从势必会妨害在欧洲阻击它的努力。
只有在其对亚洲重要性的高度推崇和亚太新边疆的大力鼓吹中,人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麦克阿瑟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其战略版图中的定位,不管这种定位是否存在巨大的误判:已经因为姑息和纵容“丢掉了”中国大陆的美国,不能再重蹈覆辙丢掉韩国和国民党台湾。
亚洲非常重要,太平洋已成美国内湖,亚洲不保,欧洲也难保,上述这几点朴素的战略判断,成为麦克阿瑟推行咄咄逼人的亚洲攻势的重要推手。
在大陆民间历史爱好者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正是因为“丢失”了中国大陆,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亚洲优先”放松了对日本的改造,并选择了重新武装日本的政策。对日本政策的考量显然不会不虑及中国大陆的情势,但两者之间是否有如此明晰直截的因果关系有待商榷,至少人们从麦克阿瑟自己的说辞中可以看到不同的解释,不妨姑妄听之。
就对日改造的方式和力度而言,麦克阿瑟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依靠日本民众自身力量并主要“借助日本天皇和文官官僚机构”来加以执行。换言之,这是一个他一开始就打定的主意,而非中途改弦易辙。也因此,他不仅从一开始就没想惩戒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甚至都不愿意主动“召见”日本天皇,以免损害后者在日本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而要“耐心”等待日本天皇主动提出要来拜会他。
此外,在日本采取和平宪法方面,麦克阿瑟也在其回忆录中强调这更多是日本人自己的选择,日本的币原首相就曾“泪流满面”地表达了这一愿望,而至于保留日本自卫的权利和力量,在麦克阿瑟看来显然是为了让日本保留最基本的自卫能力,以对抗主要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当然,这无疑也能分担美国的战略负担。
麦克阿瑟对中国大陆的态度,自然与作为一个老牌反共分子的一贯立场密不可分,此外由于长期浸淫亚洲政治并自诩为亚洲通,他毫无疑问也像亨利·鲁斯那样自负地认为对于亚洲的情势和各种政治势力的真面目比国务院那帮轻易上当受骗的家伙看得精准。
不过,从他关于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判断的字里行间里,不难发现和一味被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魅力”所倾倒的亨利·鲁斯不同,麦克阿瑟对于中国持续五十年高涨的民族主义一直保持相当警惕和抗拒的心态,而且相当精准地发现了其中的连续性,虽然其判断依据并非那么准确。
在麦克阿瑟看来,要想理解中国大陆的剧变,就必须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在过去五十年中的变化,“五十年前的中国完全是一盘散沙,也几乎不存在发动战争的倾向,因为他们仍遵循着以和为贵的儒家信条”。到了(二十)世纪之初,在张作霖统治时期,追求进一步统一的努力催生了民族主义需要。这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得到了进一步并且更成功的发展,“但在当今的政权下才真正达到全盛,以至于变成了一种全民一致性的、越来越具有支配欲和好战倾向的民族主义”。
从这一判断不难看出,麦克阿瑟并不是戴着所谓有色眼镜、简单因为中国大陆变“红”而对其产生高度敌意的。说到底,这种敌意、警惕和抗拒更多是一个刚甄于鼎盛的强国对于一个新兴大国天然的地缘战略抵触,因为后者拥有挑战自身地位的潜力和思想资源。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何麦克阿瑟的遗产至今仍拥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